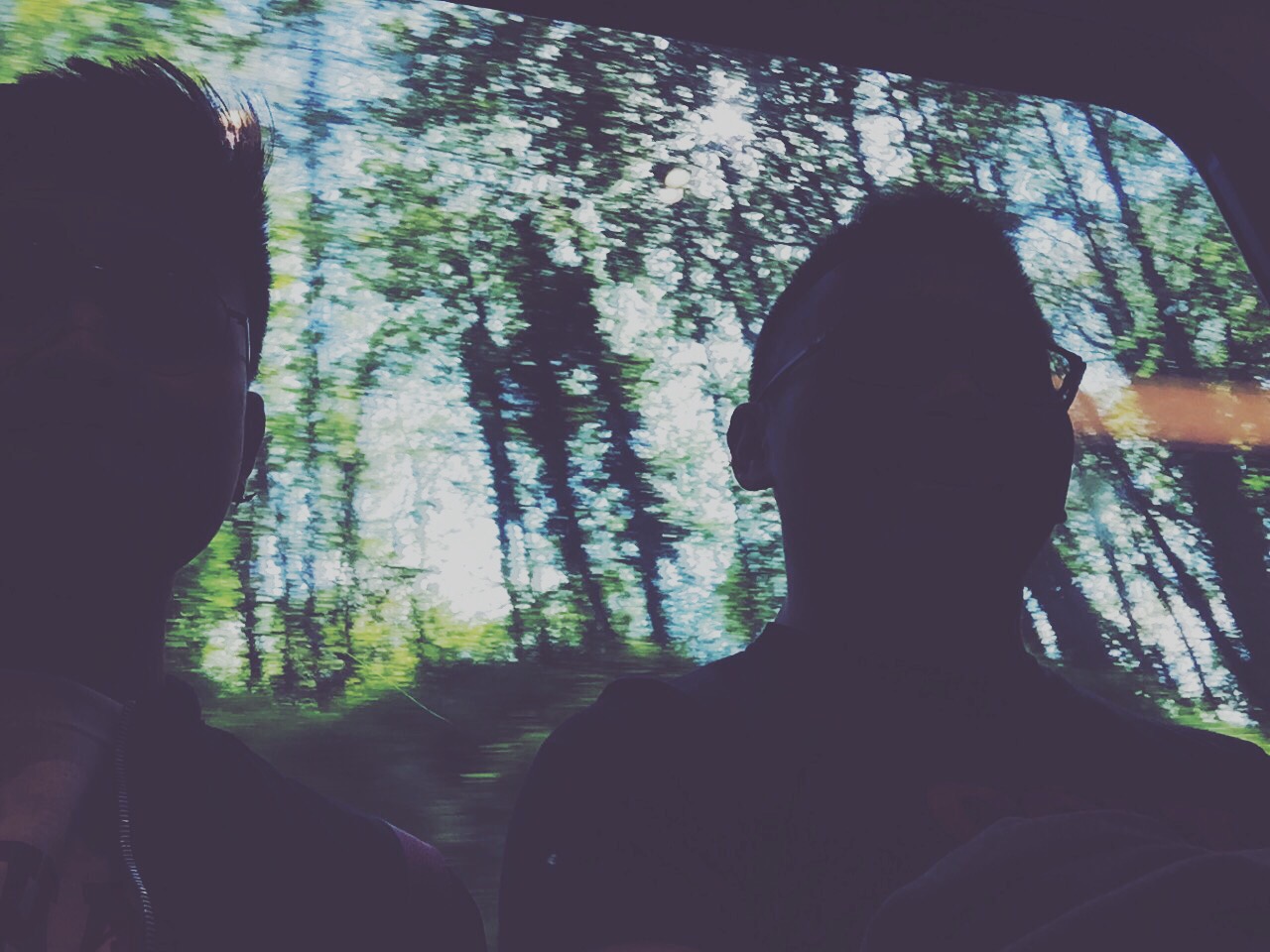两个半月前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是一辆混合动力的奥迪 A3,开起来非常安静和顺滑,我很喜欢。前阵子还和 Rick 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开去荷兰找他,然后向他抱怨荷兰的高速限速得太厉害让人开起来不尽兴。
有了车的确让我的生活有了不少的改变,这是我几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的,虽然那几年我一直在催眠自己:在有发达公共交通网络的欧洲,没有车的生活也可以很自如。但是疫情的到来还是让我下了最后的决定——我知道我是在抗拒这件事,就好像有了车,我就变成真正的大人了一样。只是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发现我很享受掌控方向同时又风驰电掣的感觉,比如在德国不限速的高速上飙到两百的时候,我的确感受到了肾上腺素的作用。
拿到车的第二周我便开车去了阿姆斯特丹,见到了 Leo 和梁海,我们在五年前吃过饭的印尼餐馆见了面。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想到原来阿姆斯特丹这么近,原来朋友们是很容易就能见到的。之后几天我开车去了荷兰的围海大坝,也开车去了海牙。在海牙散步的夜晚,我们偶遇了一个小小的社区音乐节,旁边有着一个古怪又有趣的生蚝摊,是打开着的生蚝的形状,我们买了几个,汁水吃到一手都是。再之后一天 Rick 也坐火车过来了,我们在鹿特丹见了面去参加 North Sea Jazz Festival。Laufey 有演出,这是 Rick 送我的(迟到的)生日礼物。我很享受那天下午,虽然天气湿热,还下了暴雨。我们回海牙的时候,我靠在他肩上快要睡着了。
王靖找到了新的工作,要搬去杜塞尔多夫,他搬家那一天我开车送他去了杜塞。我们从 2011 年开始就一直住在同样的城市里,现在突然要分别还是让人有些伤心。而我的博士合同年底也会结束,之后也会离开 Aachen。我也从七月初开始投起了简历,陆续接到了一些面试邀请,于是我去了一趟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中间在海德堡见到了两年没见的 Sascha,在斯图加特见到了硕士时候同学,以及认识多年却从未见过的 Feifan。和他吃完饭他送我回我停车的地方,我们又在他的车里接着聊到了半夜。“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我想,我本是不太喜欢斯图加特的,但是和他一聊完,我却对可能得斯图加特生活稍微期待了起来。只是我几个星期后便收到了斯图加特工作的拒信,而我自己也拒掉了法兰克福公司的邀请,最后接受了另一家在波恩的公司的 offer。我这才意识到我真的还要怀着复杂的情绪在北威州呆上更多的几个年头。
我在北威州已经住了八年了,这次会搬去科隆,希望在那里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同样是在去波恩面试的那天,我下午开车去了马斯特里赫特的 Rick 家,结束了和他一年的关系。离开他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我似乎再不会有任何理由和机会来这里了,瞬间眼泪充满了眼眶。我们抱着在他家门口痛哭,在等情绪稍微平复之后,我才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我却还是听到了门背后传来的哭声。好伤心啊,我不断地和朋友们重复我的感受,打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
这一周时常打开 dating apps,想寻找一些能让我分心的东西。今天白天去科隆见了一个男生,我们散了步,但没有火花。之后我便开车回了 Aachen,到家里发现他也已经取消关注了我的 Insta。我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稀里糊涂地便睡着了,其间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我的初恋突然来了德国,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十多年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讲过的什么话。我说我不记得了,他刚要告诉我,我就醒了,心脏狂跳,一身冷汗。
梁海说我很能聊,但我好像其实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看了看,写的这些内容似乎都是我买车之后发生的事情,于是我姑且起了这个标题。„Ich habe ein Auto gekauft.“:似乎是买了车之后心情刚好也大起大落,我一边憧憬着我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但又不断地被令人沮丧的事情浇灭热情,而最让人难过的事情是,我意识到自己依然还在期待着如火焰热烈的生活,就像我的青春期还没过去一样。